將出玉關得嶰筠前輩自伊犁來書賦此卻寄·林則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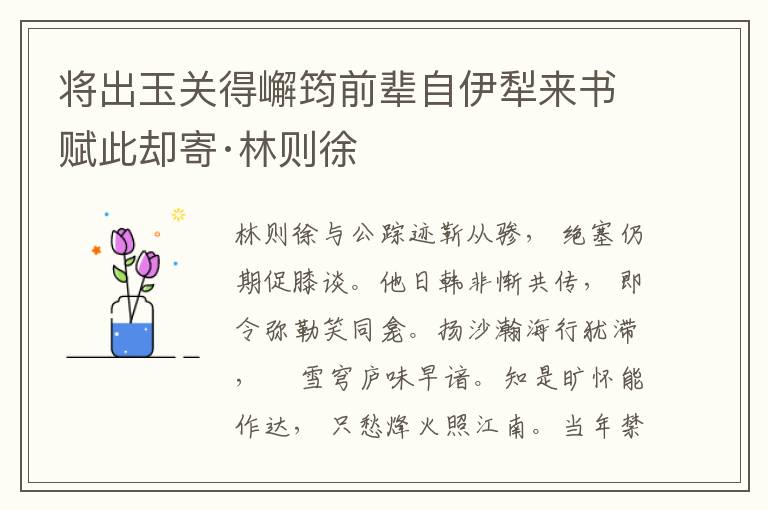
林則徐
與公蹤跡靳從驂, 絕塞仍期促膝談。
他日韓非慚共傳, 即令彌勒笑同龕。
揚沙瀚海行猶滯, 齧雪穹廬味早諳。
知是曠懷能作達, 只愁烽火照江南。
當年禁煙時的兩廣總督,決心與林則徐“共矢血誠,俾祛大患”的鄧廷楨(字嶰筠),被投降派誣陷, 已先期到達貶所新疆伊犁。1842年9月11日夜,林則徐離蘭州達沙井驛,發出一信向鄧廷楨報告西來的行程。半月后到達玉門,接伊犁來信,知這位患難知交已為他尋覓寓所,不禁感慨萬千,多么希望日夜兼程,早日到達,促膝談心,共論天下大事啊!
詩人等不得了,不禁援筆疾書,以詩代信,先傾訴一下自己的心聲。他寫好兩首詩,就叫人送走了。
這首詩一開頭就說我們倆的命運正象一駕馬車上夾轅的兩匹老馬,“靳”本是夾轅兩馬當胸的皮革,后代稱馬,這里用《左傳》語:“吾從子,如驂之靳。”(《定公九年》)意思是拴在一起,永遠分不開。從廣東禁煙到共御英軍, 一個欽差,一個總督,政見相同,意氣相投,配合默契,并肩戰斗。清廷腐敗,投降派以陷害忠良來向英人諂媚,于是他們同遭迫害,同被撤職而且同被流放到這新疆伊犁來。
然而在這“絕塞”之地,兩位患難至交并不唉聲嘆氣、愁眉苦臉,戚戚于個人之得失而萎靡不振,詩人在路上就急于盼望著“促膝談”了。談什么呢?這里沒有說,到下面讀者自會明了。
次聯說只要我們能促膝談心,那么韓非也會自慚。韓非是韓國諸公子,“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十余萬言。”后來他的著作傳到秦國,被秦王看到,十分賞識,極想得到他,“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很高興,但不敢信用,終于被老同學李斯害死于秦。這個典故和他倆的遭遇頗有共同之處,故言韓非如知我倆的忠誠,也會感到慚愧,同時暗含投降派屈身媚敵,恐怕也會落得個韓非的下場之意。用典切合情境而含不盡之意于言外。
下句極其詼諧地說,把我們這一對老菩薩放在同一個“佛龕”里“談經說法”,即使彌勒佛看見了也會發笑。遠貶絕域,本是苦事、悲事,然而詩人不作一絲一毫悲戚之態,怡然自適,隨遇而安,非有博大胸襟者決不能如此。
因為急于與老友促膝談心,穿行于萬里瀚海,飛沙撲面,阻滯行程,更令人心焦;其實我這么急匆匆地趕去,如當年蘇武那樣住穹廬,啃冰雪的塞外凄苦生活的滋味,是早已知道的。既然知道,為什么還這么急匆匆,透過這看似矛盾的心理,從更深的層次上表現出對老友的一片深情,足見所“期”之急。
最后說老朋友的開闊胸襟是我早就熟知的,即使處于不毛之地,亦定然曠達坦蕩,絕不會“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而且我更知你仍赤誠滿腔,為江南戰爭的烽火而愁緒滿懷。我急于要和你“促膝”而談的,也就是“中原果能銷金革,兩叟何妨老戍邊”(同題另一首)這件大事。
全詩以“仍期促膝談”的“期”字為線索,第二聯用示現手法設想談時和談后的情景,第三聯說自己因“期”之急,明知前程艱苦仍嫌行程緩慢,第四聯點明急欲“促膝談”之事,以交代“期”急的原因,層層契人,卒章顯志。
這首詩又是代信的贈答之作,既說對方,又說自己,尾聯則明說對方,暗說自己,一筆兩面,把兩位抗英志士共同的崇高品格,共同的坦蕩胸懷,共同的深切思念,共同為國事而愁緒滿懷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憂國憂民之赤心,和時代的脈搏一同在詩中跳動,激蕩出一股愛國的浩然正氣。
語言平易明白,風格悲壯蒼勁,有如偉岸的青松,百折不撓,傲然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