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孕育于土地中的和諧與美——李進祥鄉土故事的生態意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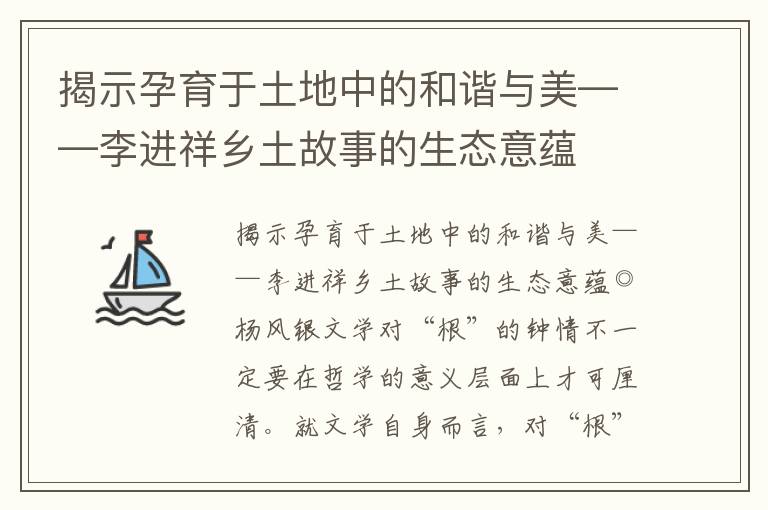
揭示孕育于土地中的和諧與美——李進祥鄉土故事的生態意蘊
◎楊風銀
文學對“根”的鐘情不一定要在哲學的意義層面上才可厘清。就文學自身而言,對“根”的尋找和表達成為文學自身律動的一種體現,無需對其溯源,更沒必要講出這一現象的出現動機。鄉土文學更是如此,只是新世紀鄉土文學的表達出現了其“獨有的文化癥候”而已。“新世紀以來的鄉土小說在城鄉關系發生巨大變化的歷史背景下,其表現內容、人物形象特質、作家的敘述情感等與以往的小說創作相比,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意味著我們面對的鄉村現實及其文化出現了新的因素,帶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諸多復雜關系,而且意味著作家在理解、表現這種關系時的思想、立場、敘述情感等也有了不同于以往歷史時期的內涵。”(王光東:《新世紀鄉土小說城鄉關系新表達》,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9月10日)。鄉土故事里人與鄉村,在本源上即為人與自然的關系。鄉土敘事就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審美表達,揭示人作為能動個體在自然環境鄉村里的人事變遷和與自然的互動影響。鄉村歷史,在本質上就是人在土地上繁衍的歷史,就是人對土地情感的積淀過程。一定程度上,鄉土情感的形成就是人之于土地的精神史。在城鄉變遷的潮流里,鄉土故事對土地精神的審美表達,就為當代文化語境里的人對鄉土作為“根”的認識的審美表達。
在新的“文化癥候”下,對鄉土故事的講述,是必然涉及諸如“城鄉變遷”“文化沖突”“鄉土文化荒蕪”等內容,總有一些略顯懷舊的影子一直揮之不去。李進祥的鄉土故事尤其鮮明地表現了這一“根”文化特質。在城鄉變遷中,尤其在寧夏這一地域文化特色鮮明的地方,包括“進城”“生態移民”等時代變遷大面積出現,文學要對這樣的時代做出反映也是必然的,同時對于“城鄉變遷”而生的“斷裂”、沖突的文學表達,要想做出適于文學規律的表達是有難度的。基于“大地精神”的鄉土敘事,挖掘出蘊于土地的“根”文化內涵,是李進祥鄉土敘事生態主題的追求。
鄉土地域作為“根”文化的母體,是李進祥小說生態意蘊表達的基本敘事場。鄉土人情、地域風俗里的生態意蘊是李進祥這一類小說故事的基本內容。
鐘情于土地的故事講述,從《口弦子奶奶》到《換水》,都有這一特點。
人與土地的緊密關聯,不關乎高貴與低賤,而關乎人之為人的本源性狀態:在原鄉土地上的人,是有鄉野人生存的卑微,但具備人生存的基本尊嚴。都是為生存,涉及婚姻愛情,但口弦子奶奶作為一個讓全村人都覺著“惋惜”的形象,以極富穿透力的口弦子震顫著現世的人生。隱忍在《口弦子奶奶》里是被“前置”的,將一個忠于愛情的題材處理出“心痛”的主題,獨到地顯現了李進祥鄉土故事主題的“深邃性”。這類故事主題的“深邃性”,也是鄉土生態的一個表現:割舍情感而忠于生存!《換水》將人物置于城鄉轉換的語境,講述謀求幸福的故事,而“謀求幸福的故事”外殼下,卻是鄉土生存的淳樸對城市生存的嚴重“水土不服”的內涵。這種將人與原生土地的“親密關系”以城鄉生存狀況對比的框架承載,很有韻味:鄉村生活的單調和干凈,城市生存的復雜與艱難,卑微人物命運的不可自我掌握,難以承受的辛酸,墮落的悲劇,等等。這些故事本身極富時代氣息,讓現實生存擁有厚重的歷史感。李進祥小說對“清水河”這一鄉土地域上的風物人情的精細書寫,藝術地呈現了其所承載的大地精神生態。
鄉土故事里的日常構成了李進祥鄉土故事講述的主要內容。
小說《奶奶活成孫女了》講述奶奶與孫媳婦的故事。坐月子、種園子、養牛,如此普通的日常是這篇小說的主要講述內容。以鄉土生存最為熟悉的生長故事起頭,將“新”與“舊”的沖突置于新媳婦與婆家奶奶關于坐月子的不同觀念這一“熟悉”語境中,結局是悲劇,老舊觀念的勝出是以時間為銳利武器的,孫媳婦對奶奶的尊重是在這樣的沉重代價中建立起來的。綿綿土,這個鄉土世界里最“管用”的“材料”支撐了鄉土生命最初的安全,鄉土智慧的積累也只能在時間中被切身認知,無書記載,無書可讀,“看”和“經歷”成為其基本的形成特征。孫媳婦的教訓可謂慘痛,故事本身也慘痛,讀者的閱讀感覺也酣暢。而這一事件的講述,是悲劇框架下對鄉土生態智慧的一種最藝術的表達:人對土地的倚重,鄉土地上的人與“土”的親密關系,離開土地生命就會受損……《奶奶活成孫女了》是對《換水》主題的“原鄉講述”,是大地精神的“重講”。
種園子,是鄉村生活的基本內容。奶奶的園子是時間的積淀。
奶奶說,她十四歲上到這家來,做童養媳。正好鄰家挖棗樹,挖出幾棵小苗,晾在那里。她看著小苗上細碎的葉子綠瑩瑩的,心里一動,就張口要了棵棗樹苗。拿回來栽到后院里,樹苗就活了,長大了,就在她和爺爺圓房的那一年掛的果。棗樹好活,自己會繁殖,過幾年,大樹周圍又生出更小的樹。一顆棗樹,洇了一大片,成了果園。
對生命的尊重就是對時間的認可和尊重。鄉土生活的純凈品質就如小說描述的這般:遵循生物生長的生態法則。日常生活的經歷,其基本內容就是在時間里沉淀出生命的品質,錘煉出生命成長的能力,懂得生命就是在時間的河里向前延伸。自然法則在鄉土地上的恣意,結局不是荒蕪,而是茂盛。這在現代環境危機和生態問題突出的時刻,是個寶貴的品質——守正了文學表達近于終極的關懷。
《奶奶活成孫女了》還講到了奶奶種不動園子后養牛的故事。
奶奶喂牛,從不用飼料,就是草和糧食。不干凈的東西,也不給牛吃。奶奶說,牛是大生靈,通人性呢。給它喂了不干凈的東西,人要擔罪呢。
奶奶一年就喂一頭牛,牛肉好吃的消息就傳開來了!食品品質的好壞,是不是遵循了生命成長的基本規律,都在小說精細的敘述里被淋漓盡致地再現了。綠色、生態、環保成為時代主題的時候,小說在故事情節里如此精細的表達,是作家高尚情懷的一種體現。
工業科技的發達助長了人類“自我中心意識”的膨脹,在面對自然的時候,會表現得狂妄自大;對待自然的時候會粗暴,表現出對自然規律的蔑視。而在鄉村,工業科技的影響相對較弱,鄉土地上人會在自然的影響下表現得非常“順從”,依據自然的規律生活成了鄉土地上的人民的基本品質,依據自然的規律種植,認識土地的性質,盡力去在土地上生活下去。鄉土自然的規律讓鄉土地上的人們具有一種謙遜的態度。這也是李進祥小說里的主題之一。
奶奶的棗樹園子任憑棗樹恣意生長,只有瘦小的奶奶能夠在其中自由進出。鄉土地上的生存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最本真的體現。鄉土大地這一生存環境塑造了鄉土地上人們的心靈結構,鍛造了鄉土地上人的憨厚品質,他們懂得“討生活”的前提:尊重土地,對大自然心存敬畏。好生活是土地對人的恩賜,除了勤勞不能有別的過高的奢求。鄉土社會的精神由此產生,得到傳承。《奶奶活成孫女了》里的奶奶,就是鄉土地人民的典型代表。不怨天不尤人,一生里一直勤懇勞作,用鄉土地上人老祖輩傳下來的經驗造福子孫后代。
李進祥筆下的鄉土世界,以藝術的工筆細刻著鄉土世界里的生存智慧,生態智慧浸潤在這些豐富的生存智慧中。在當代工業背景下,顯得那么稀有和珍貴。
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大多表現為人向自然的大肆掠取。《遍地毒蝎》就是通過鄉土地上的人在向大自然大肆掠取的時候,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而生成了悲劇。原來鄉土地上人與自然物各得其所,相安無事。將“母豬”帶進人居環境,對人的侵蝕是必然的結果。中毒甚至失去生命,是對人的一種警示。雖然假想人可以更細致一些,讓“毒蝎”不得接近哈桑,但故事被講述出來就變成了事實,結局是唯一的,永遠不得更改。工具理性盛行的時候,因算計而“利欲熏心”,而膽大妄為,而忘乎危險。李進祥在這類題材的小說中,以慘痛的教訓為代價,傳承了鄉土地上關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屠戶》與《遍地毒蝎》的故事類似。民間諺語“自作孽不可活”被普遍念叨和認可。在面對利益和攀比、誘導的時候,屠戶沒有禁得住。勤勞、善良,以至上進,都在屠戶身上全面體現,謀求生機、追求幸福本沒有錯,而一旦違背了為人的良心,違背了牛生長的規律,該有的報應遲早會觸及自身。馬萬山,一個忘記名字的普通進城人員,老黑,一個精于算計的“道上人”,一個“方子”徹底改變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建立了新的“索與取”、勞與資的關系。悲劇的前提也在悄然地形成。這種“制作精巧”的故事以警醒世人的“形式”表明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建立的重要性。牛吃天然草料是自然規律,違背了這個規律會遭殃。“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種與自然共命運的意識,不只是文人筆下的文雅表述,在鄉土地上生活的人的心里,更是一種種族記憶,一種被遺傳下來的集體無意識。家禽、家畜,是人們鏈接自然的最親近紐帶,讓他們按照自然的規律和樣子完美生長,與人為伴。
《狗村長》同樣將故事置于城鄉變遷、移民進城的語境下,講述人情淡漠。但這樣的故事框架承載的卻是一個深刻的生態主題:通過人與狗的親密關系凸顯,揭示山村荒蕪之后,親人離去,人與狗共同遭遇的危機和孤獨,以狗的進城、返鄉為依托,將城鄉變遷細致入微地再現出來,空巢老人德成老漢的形象也在人與狗共生的語境中活現——人與狗的親密關系得到了最得體的存在。
他忽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緊緊的腳步聲,終于有人進門了。他側過眼睛,沒看到人,卻看到了黃狗。黃狗嘴里叼著一只兔子,頗有些得意地望著他,看到他的眼神,黃狗努力地把野兔子送到他的頭邊,還用嘴往前拱了拱。德成老漢看到兔子的頭血淋淋的。
人事變遷形成的創傷和裂痕,最后在人與狗的溫馨場面中得到愈合:空巢老人德成老漢對村子的守候和黃狗對村子的守候一樣,其中所表達的相依為命的主題浸入人的血脈。
現代社會,城市與鄉村不只是兩種空間形態,不只是人類生存的兩種狀態,且是人之存在的兩極。人在這兩極間游走、徘徊,上演出走、返鄉的故事,悲歡離合就承載在這些故事里,人類心靈深處對自然的眷戀與對故土的依戀融為一體。鄉土小說講述鄉土故事,從美學的角度描述人與土地的關系,通過“鄉村”這一地理上的支撐點,讓人們擁有精神上的支撐點。找到鄉土這個特定地點,充滿愛心地投入生活,使自己與腳下的那片土地融為一體(程虹:《尋歸荒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7月,第201頁)。
2017年的《夜半回鄉》就表達了這一命題。
三個身份不同、職業不同、人生境遇不同的人:王薔、馬龍、楊生才,教授、局長、老板,一個偶然的機緣湊巧坐到了一起,“各懷鬼胎”,讓人意外的是,他們會形成一個共同的想法:半夜回鄉。理由很簡單:想回村子看看!王薔這樣一個本不是“烏雞溝”的人,卻也擔負回村看且是半夜看的“責任”。剔除了一切風險之后啟程,恰就是一時沖動,為人們縫合了因離鄉而撕裂的傷口。“烏雞溝”這樣一個鄉村“具象”承載了大多數人的“原鄉夢”,揭開了現代人在心底深藏的對自然的不舍與眷戀。
三個人又走了一陣,東方就發白了,山的輪廓顯出來了,山卻更黑了,漫天的星星也變暗了。盡管暗了,王薔還是覺得很亮,這些年在城里,他從來都沒有看到過這樣藍亮清明的天空。他仰望星空,慢慢落在后面了。
黑夜和星空給了王薔久違的舒展感,城市生存的緊張在鄉村的夜空下得到了緩解,這或許才是真正意義上對故鄉的皈依:找到心靈與環境的天然契合。我們在這里不討論王薔這個人物名字里的寓意,小說借此實現了鄉村對人心靈上的慰藉,對“回鄉”這一現代人的精神需求完成了講述。
李進祥在對這一類題材的處理上,都是反向的:講人與自然的不離不棄,卻以“返鄉”這樣的故事作為呈現載體;講人與土地的親密,卻以“離鄉、進城”這樣的故事作為呈現載體;講人與鄉土的親密血緣關系,卻以人與狗相依為命的故事作為呈現載體。一定程度上,這種反向的講述方式,成為鄉土故事里生態主題呈現最恰當、最“美”的方式!
楊風銀,文藝學碩士,魯迅文學院少數民族創作培訓班27期學員,發表評論、詩歌、小說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