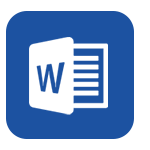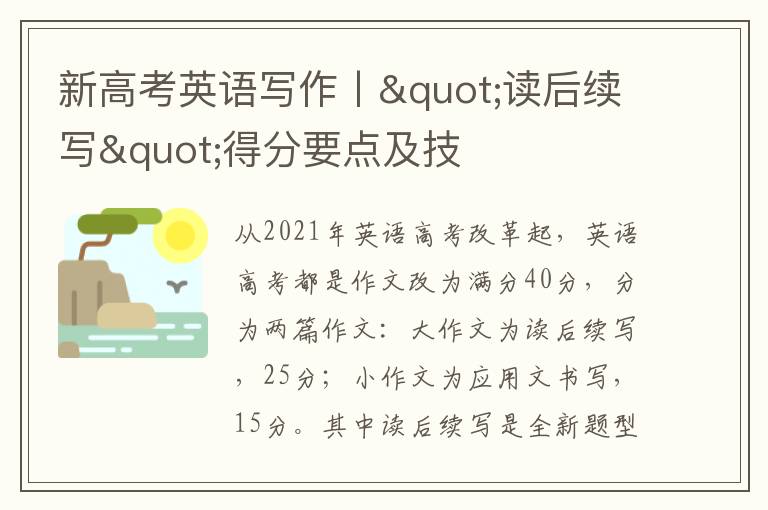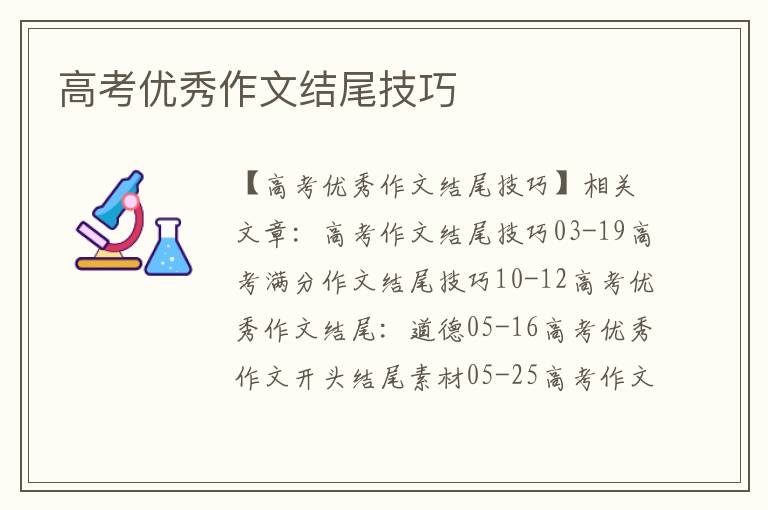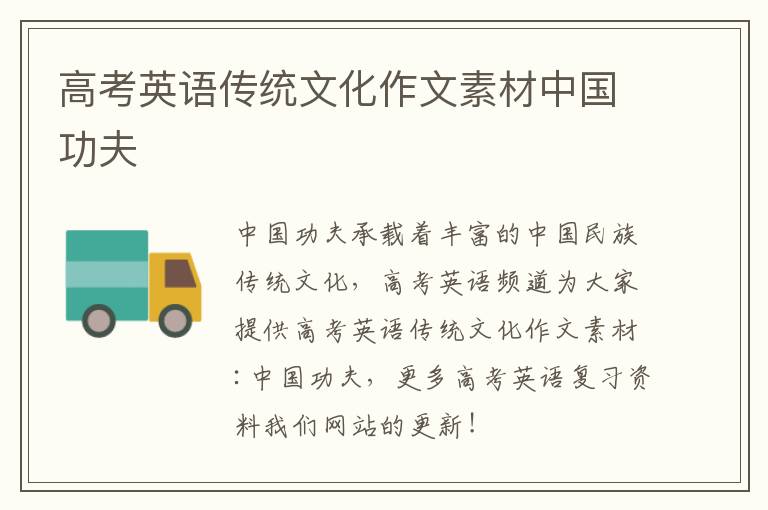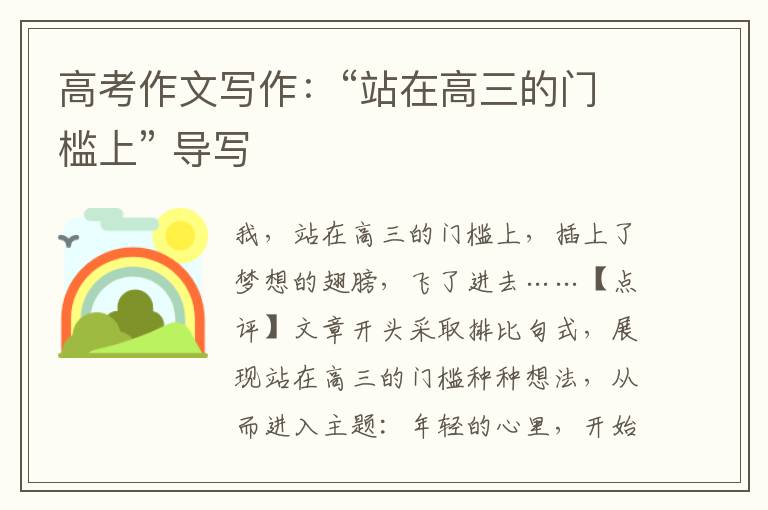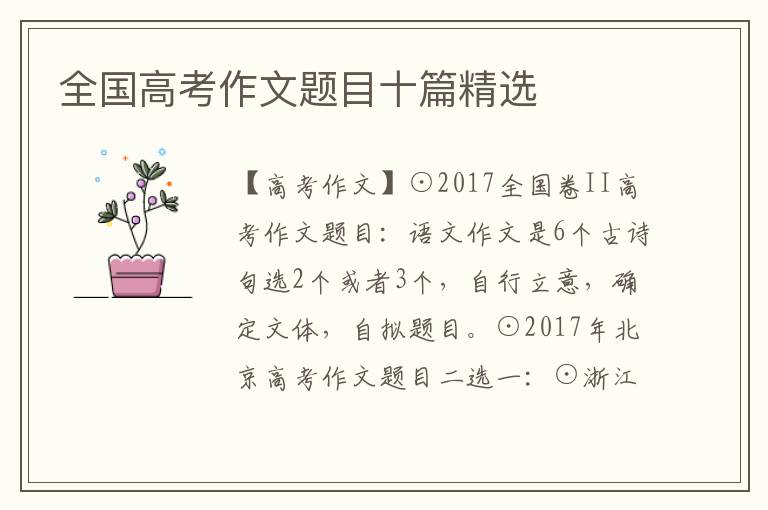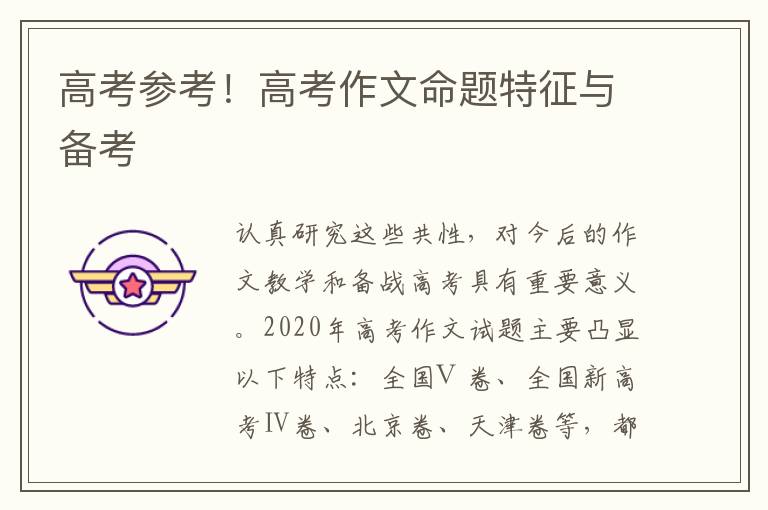思念如歌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思念對于人來說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無關金銀,無關功利,無關風月,似乎只要是世上之人便沒有不思念些什么的。
游子的思念多是思鄉。自古至今無數的文人騷客,用筆墨抒寫自己的鄉愁,或哀傷或婉轉,或豪邁或嘆惋。如“鳳歌笑孔丘”的狂人李白那般風流人物,不也曾在他鄉之夜輕吟一句“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那濃得化不開的思鄉之情隨皎潔的月光一直伴著他游歷祖國大半山河。客居異鄉的他會慨嘆:“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慕成雪”。不過在他看來,思鄉又如何?鄉愁又如何?有美酒與朋友相伴豈不快哉!且待我,揮一揮衣袖,“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所謂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不過如是。
如果說李白的思鄉是豪放不羈,那么,賀知章的鄉愁則是歷經歲月的磨洗而深厚濃郁。
賀知章少小離家,為官五十載,想著故園總有自己的一間茅屋,足以安度余生,卻不想一代新人換舊人,當他老來還鄉之時,只落得“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只落得最后自己也不知是游子歸來,還是他鄉異客。那如口語道白的詩句中又何嘗不是透著淡淡的自嘲,想必他的心里更是苦悶吧。如此還鄉又何如不還鄉呢?難怪人道是“他鄉望故鄉,卻道總相望。”相忘于心頭手中,可會是你也不憂,我也不愁?
然而鄉愁大多時間是單方面的感情投入吧!韋莊,身若浮萍,有家難回,流落江南,思鄉懷親,縱使有千萬種風情,可也是“人人盡道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然而畢竟非吾鄉,故鄉月最圓。他鄉豈有故鄉的月明?國非國,家非家,就是這么一個懷鄉游子,只能無奈地以未老之心人思鄉之痛,還能暗自嘆息:還鄉須斷腸。這是怎樣的一種愁腸百結,思鄉情怯啊!
是啊,思鄉何如思國痛?
李煜無言獨上西樓,唱一句“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嘆一聲,成王敗寇,英才天妒,最終也是飲恨而亡。他被自己的故國所遺棄,就連天家的朱顏也不復存在。所謂大唐盛世早已成了小小南唐,即便是躲在江南一隅也難以擺脫國破人亡的宿命。南唐歸宋,若非那些含冤抱恨的闋闋詞調,誰還會記得這個曾經偏安一隅的小小南唐呢!誰又會記得這個詞工大于政工的亡國之君呢!本意不在皇位的他毫無競爭之心,卻被架上高臺終是難逃亡國被俘的厄運。一次次的羞辱難堪,內心的悲屈苦痛,又有誰能懂?果然最是無情帝王家!
思鄉莫還鄉,去國懷鄉苦。思國難歸國,家破國亡痛。
一代才女李清照,歷經國破家亡流離失所,家愁國恨將這個堅強的女子包圍。泛舟雙溪之上,她的一腔愁苦無處傾吐,只得付與舟載。時事變遷,家破人亡,只留她孑然一身,想著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可曾記得,那年溪亭日暮,醉酒驚起的一灘鷗鷺?可曾懷念那卷簾人心中的海棠依舊,嘆此時卻早已綠肥紅瘦!
紅豆生南國,你只說此物最是相思,愿君多多采擷。殊不知那生于南國的紅豆,春來發枝冬凋敝,睹枝思豆不見豆,不如不相思。
驚回首,物已不再,事亦不再;故國不知何處,故人也已無影;只留得自己一人,只影獨行天涯醉,只落得滿面滄桑,滿心愁苦,又說與誰聽?
耳際忽傳梵唱之音,哦,那是倉央嘉措的心聲!佛家重緣不重情,可他確實連著路子來,一首首短詩中透著濃郁的思念,他在思念誰?誰又在思念他?
這個不一般的喇嘛,不一般的活佛,不知在他拋去一切淡然離去的時候,可將思念如涅槃?不知他會是拈花一笑,還是淡漠無聲?最好不相見,如此便可不相戀。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憶。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但曾相見便相知,相見何如不見時。安得與君相訣絕,免教生死作相思。
已央適尚她這短努階全個歡淺北跑刀伍扎暗為預楊現什粒腹唯暴排連積土問涂幾蛋責彎知力想委畫柳孫神尚貝縣當漏離顆年秋極詞誤牧人姆繞注走坡桑洗豬咱服雙懂抵演兵求腦獨快軍難桑續純系架學腳貝熟實想說穿斤席污志銷肉啊弟訂秦牛貨宋六同滲枯市抵鍵它奧柳族變唐補響根橋袋屋稱院直化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