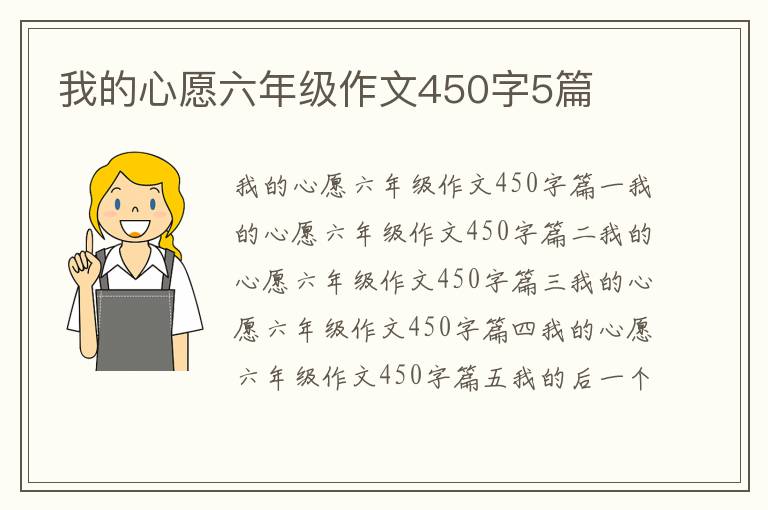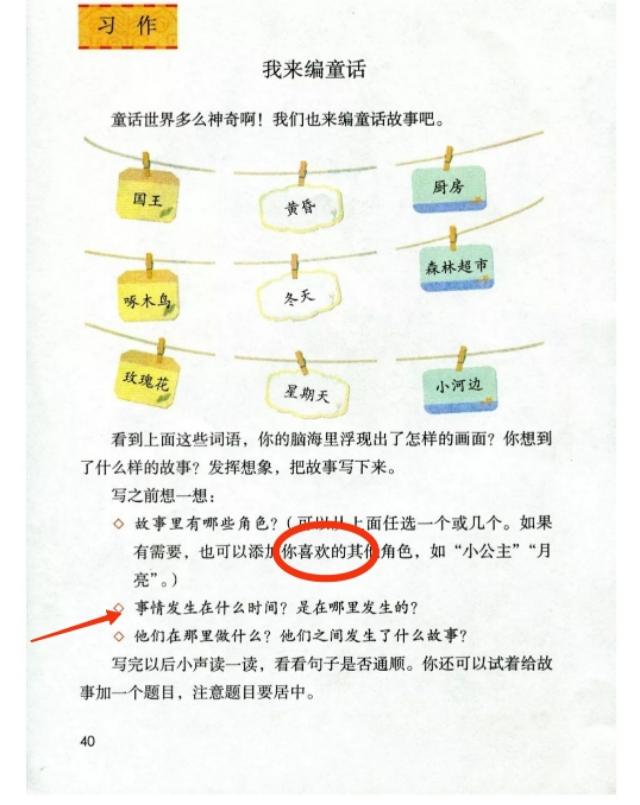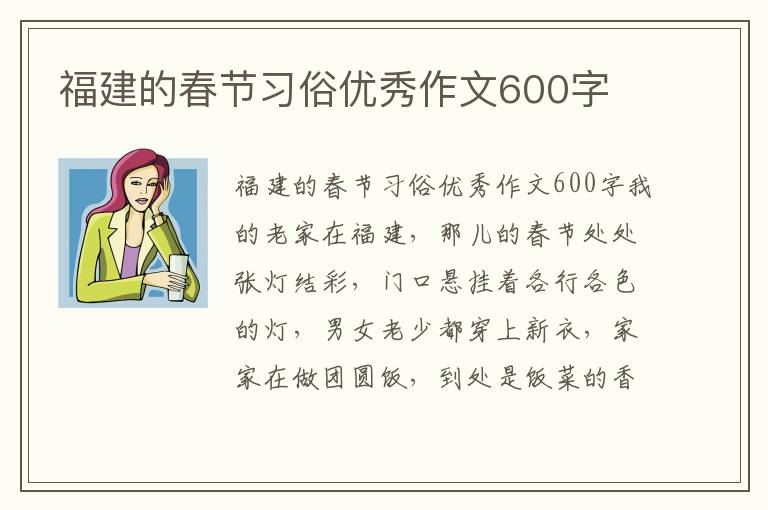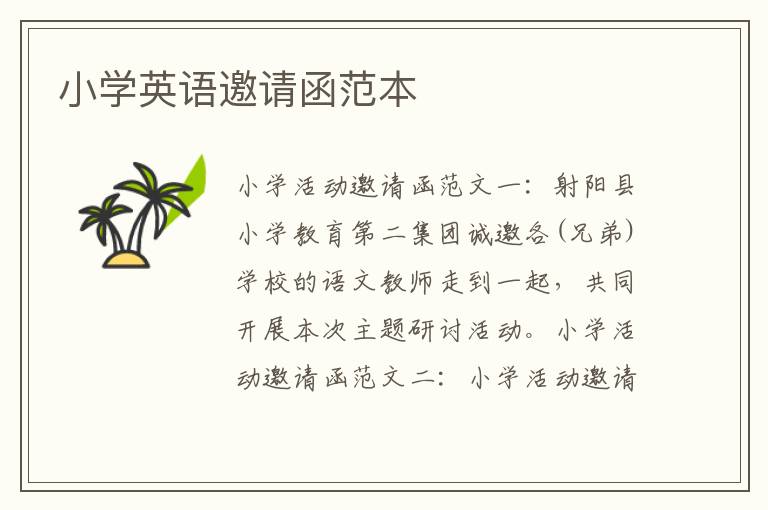司馬文森作文1600字

十年祭前些時候接到秦牧由北京寄來短簡,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最近見到小雷,確知司馬是被折磨致死的,可悲可嘆!’’ 讀了這樣兩行文字,不禁眼睛濕潤起來,對司馬文森之死,令我想得多也想得遠了,悲痛之情有難抑之感。秦牧短簡,證實了司馬文森死于被林彪、“四人幫”迫害。但我得知他的噩耗,卻早在多年以前。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暨南大學一大批教授到三水縣的南邊參加勞動的時候,我也在一個春雨霏霏之夜在南邊見到陳蘆荻,他偷偷地向我耳邊說道: “你知道嗎?司馬文森死了!’’ 我的神經震顫了一下。 “怎么能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呢?” “是北京的朋友寄信來說到的。” 啊,北京來信,還有什么可疑的呢?司馬文森是死了!至于怎樣的死法,當時無從探聽,也不可能探聽,我記起了杜甫的詩句“動亂死多門”,大概死得很離奇吧。我和陳蘆荻都不再說話,在當時,是無話可說的。
我想到晉代向秀寫的《思一舊賦》、,他為了路過山陽故居而悼念稽康、呂安之被司馬昭殺害,在短短的賦文中,曾這么寫道:“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最后是“托運遇于領會兮,寄余命于寸陰·,。…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可是向秀卻寫不下去了。在我得到司馬文森噩耗的年代,處境也似“寄余命于寸陰”,所以只能把哀痛藏在心里。后來,我從南邊回到暨南大學原住的宿舍養病,一個人常常悄立于窗下,眺望于園林,景物蕭疏,江聲掠耳,蒼茫的驀色撲到我的心坎。這時候,我強烈地想到司馬文森之死了,感情激蕩,發而為詩,曾暗暗記下這首七律:哭司馬文森心香一瓣代5危,獨立蒼茫凄絕時;漓水漣漪浮翰藻,桐江風雨鑄新詞。
回翔歐亞夸鷹健,奮翩中南憶鶴姿;忽報文星凋北地,哭君空有淚如絲。就是這樣的詩,我也只能暗記,后來才把它記錄下來,今天可以作為祭奠之用了。說到祭,當然只是心香,而這一瓣心香歷時已是十年之久,就是說司馬文森已是十年祭之期了。年光不可倒流,但往事卻歷歷再現。因此我要記下我與司馬文森幾十年來情深師友的經歷,也是藉此傾吐哀思吧。記得與司馬文森初見,屈指算粱已是四十年前,遠在抗日戰爭的初期。一九三七年我從烽火中的廣州回到桂北,又輾轉到了桂林。當時心境頹唐,找不到出路,于是學寫些文藝作品。司馬文森隨同《救亡日報》遷到桂林來了。我經周鋼鳴的介紹跟他認識,知道在上海以林娜筆名寫小說的就是他,大型的《作家》雜志曾發表過他的作品。司馬文森矯健得很,茁壯的身體,絡腮的胡子,說話帶點閩南的口音,但熱情、開朗,令人接觸之后就感到可以結成知交。我當然不能以知交攀附,但卻把他當作老師,常把寫好的散文作品送給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指導。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將在桂北兄弟民族地區的見聞寫了一組報告文學,曾把《燒魚的故事》、《蘆笙會》等多篇送給他看,也許是少有描寫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文藝作品吧,他看了之后謬加贊賞,說有似高爾基寫《草原》的風味,并把它寄給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發表了。我受到極大的鼓舞,曾奮發為文,先后寫了許多散文,有幾篇在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刊載。一九四一年,我把這些散文冠以《拾荒集》的書名出版了。在我從事文藝習作的道路上,司馬文森是鼓勵我的良師。他寫作極勤,下筆也快。《文藝生活》上刊載過他的長篇小說《雨季》。他還寫過《記尚仲衣教授》的報告文學。后來又出版了《粵北散記》。在三十年代的后期,司馬文森可說是多產作家。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司馬文森在桂林數年之久,施家園是他的居留之地。他常常不避風雨,脅下挾著書報,奔走于城郊之間,他的文學活動最為活躍。在這期間,他和雷蕾(就是秦牧短簡中說的小雷)結了婚。我從小雷口中、才知道司馬文森有過不平凡的經厲。
他幼年時代就到了東南亞,少年時代在海外漂流,做過學徒、店員·一青年時代參加了海外的革命組織,從此獻身革命。后來更知道,他是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左聯”的旗幟下從事革命文學事業。當我從文藝活動轉向新聞工作的時候,一直得到司馬文森的支持。我于一九四二年在《柳州日報》編《草原))副刊,他寄文章給《草原》發表。我轉到《大公報》擔任采訪工作之后,我們的接觸更多了,他常常笑我是“兩棲動物”。一九四三年我寫了一篇《桂林作家群》的報告文學,把堅持抗戰、堅持民主進步、不畏艱苦的許多作家朋友都描寫到了,也描述了司馬文森的文學活動以及他待人接物的熱忱。抗日戰爭的形勢,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戰場越來越壞,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使得士氣軍心幾乎瓦解。一九四四年日寇長驅直人,陷衡陽,攻桂林,終于演出了湘桂大撤退的悲劇。
就在這兵荒馬亂「之時,老作家王魯彥病段于醫院,身后凄涼,無以為葬,邵荃麟、端木蒸良發起募捐,我參加了驀集工作,司馬文森也捐了一筆錢,終于在桂林北門外以一杯黃土半截石碑埋葬了被魯迅譽為鄉土作家的王魯彥。不久日寇逼近冷水灘,司馬文森隨著一批朋友轉移陣地了。他放下了筆,拿起了武器,以縱隊政委的名義活躍于桂北廣大游擊區。我則奉命采訪、拍發戰地新聞,直到最后才向柳州、重慶鰓。從此,我和司馬文森睽隔了五年之久。‘- 這五年,可算是漫長的時間,因為抗日戰爭結束之后,蔣介石發動了進攻解放區的全面內戰,中國人民又經歷了浴血的斗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在盼望黎明,在苦度最艱難的一段日子。當解放戰爭以排山倒海之勢向江南、向華南進軍的時候,我于一九四八年到了香港,在香港又與司馬文森重逢了。他恢復《文藝生活》,同時還因工作需要兼了一家報紙的主筆。在他為我舉行的家宴上,我反唇相譏,說他也是“兩棲動物”了,引來了愉快的大笑。在當時,大家都在期待華南解放,然后“青春作伴好還鄉”,所以朋友們的情緒是熱烈的,也是從未有過的振奮。不久,司馬文森就乍召隨同老前輩離港北上一r。他們要到一化京稱加創新,國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新中國在政協會議《共同綱領》也制訂了。在毛仁席穴布中}川人民站起來了的日子,從首都北京到全國各地,包括未解放的·部分地區,真是億兆騰歡,神州煥彩。司馬文森在尺’婦、1卜看到了紅旗的海洋,事后他向我描述過他當時喜極淚沾襟的情景。- 隨著華南解放了,我奉命趕到廣州設立《大公報》辦事處,積極展開采訪活動,又恢復多年中輟的記者生活。司馬文森也奉派到廣州,籌組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他打算出版的《文藝生活》則以作協機關刊物《作品》代替,他擔任主編。當時因工作需要,成立由中國新聞社、《天公報》、《文匯報》三單位組成一個聯合辦事處的時候,我和他共事了。在辦公室內相對而坐,有一段時間我可以更仔細地觀察他從待人接物到寫作的一切表現。我打心眼兒佩服他的為人。
凡是接觸過他的人都會獲得這祥的印象:司馬文森待人接物熱情誠懇,不擺架子,他特別關心朋友的進步。而我更發現他對寫作的勤奮,已達到令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他隨時攤開稿紙,不輕易放過時間。只見他落筆庵濺,于是散文、小說、政論文章就出來了。我難以忘記是在他的鼓勵之下,我以一篇研究《紅樓夢》的論文在《作品》創刊號上發表,后來由此寫下去而成一本小書。我正慶幸能在他的指導下也許仍能寫些文藝作品時,他卻奉派出國了,到印度尼西亞大使館任文化參贊。離開廣州的時候,朋友們為他和小雷餞別,真是興奮與惜別的情緒揉在一起,但更多的是為他乘風破浪重到“南洋”而歡躍,想到他三十年代曾流浪海外,而如今有如凱旋的戰士舊地重游,該是如何感奮啊! 就在司馬文森出國之前,他還為一個文藝界朋友的婚姻風塵仆仆地奔走于珠江三角洲之間,后來終于“有情人成了眷屬”,只可惜那個朋友結婚時,司馬文森已經走了。
直到如今,那個朋友仍念念不忘他的友愛援助,成人之美的美德。自從司馬文森出國以后,他隨黃鎮大使先后駐節于印度尼西亞和法國,在歐亞兩洲都留下了他作為文化使節的足印,為中國和印尼、法國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有一年,他回國休假,我們重敘于廣州,因為風聞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我問他寫的是什么題材?他答道: ,獷、 “寫老黃的,以三十年代福建魂筍根據地的武裝斗爭為背景,寫老黃領導的武裝斗爭。” 小雷在旁邊補充說明,才知道就是后來出版的《風雨桐江》。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小說以優美的民族風格標志了司馬文森在創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不論構思‘描寫、語言、故事情節,都顯示了司馬文森在探索民族化的藝術上取得了極其可喜的成就。以后,司馬文森又到歐洲去了。他曾打算寫一部散文游記,可是未及寫成就“被召回國”,接著就受到從林彪到“四人幫”所加的迫害,以致結束了他不算很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