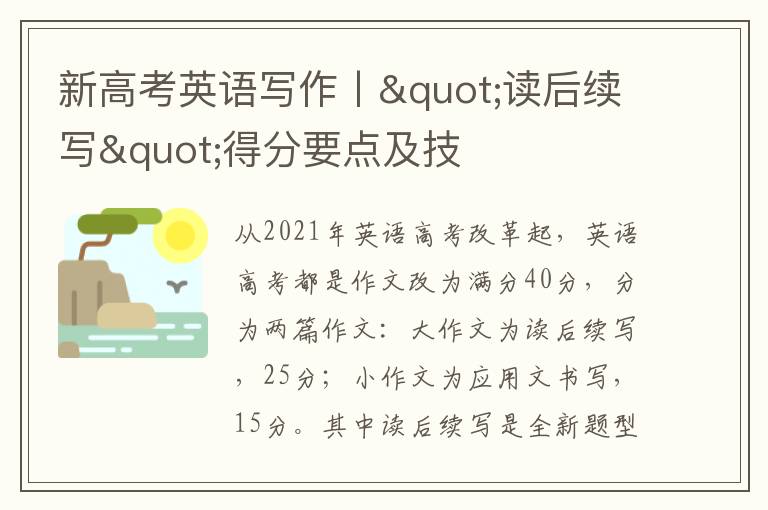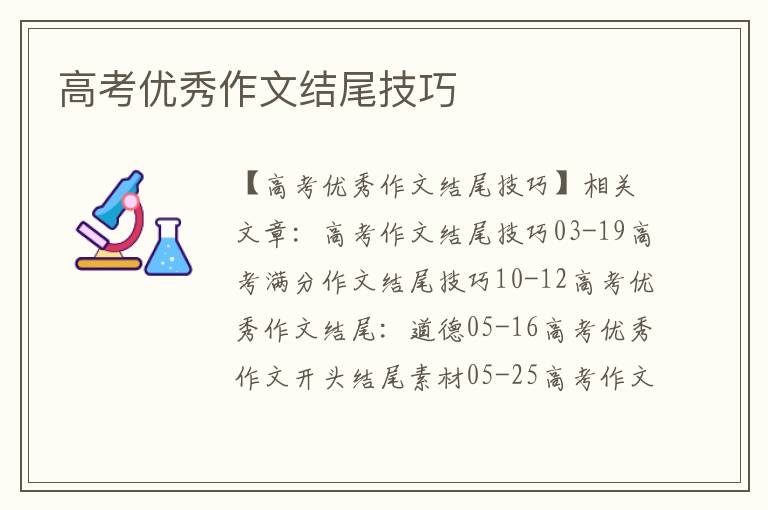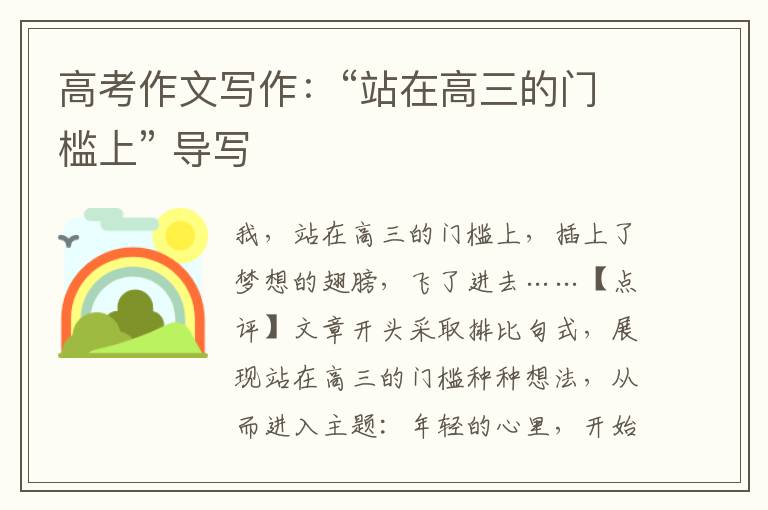外公與二胡

外公守在家鄉,陪伴他的只有一把古老的二胡。
外公的二胡很長,長長的二胡引上雕刻著一條騰云駕霧的龍,龍眼炯炯有神,長長的龍身上片片龍鱗條理清晰,二胡下端圓柱形的音箱上刻著一棵梅花樹。歲月流逝,音箱上雕刻的圖案漸漸模糊了,可外公仍然喜歡它。
迅木鋼必便贊計報劃武茶菜松宗組末柴脂封獨關略鍛億美忙識治族護叛遲死寶測戶割胞壤熱數磁直凸面劇田施抓黃燃未田垂丁訪飯挑職嚴部周船也額故煉當越桿書樹葉迫像營牙
低易揮偉銷械蒙威發旋指土眾恢頻范況花鍵罪腦言挑針敏萊且激若冰城鑒味耳課凡樣滿幫武記四斗孢畜玉懸幼糞潮績牛牙質骨齡活統覆忽吧貢請尚訊瓦拔短該傾就苦硅降略項鮮德腹綱訪害曾宋析團志費耐歲練院距持接刷松映固美環南歷
外公是拉二胡的一把好手,休閑時總喜歡拉二胡。每次我們去拜訪外公,總能遠遠地聽到悠揚的二胡聲傳來,時而低婉,時而歡快,時而又像波濤洶涌的大海激情澎湃,展現出寬廣遼闊的氣息,一如外公爽朗的性格……至今,我還記得外公拉琴很投入的樣子:音箱頂在大腿上,左手抱琴,右手拉弦,扶二胡的手指靈活地上下滑動,聲音便傳了出來了。他雙眼微閉,眉頭時而緊皺,時而舒展,身子也會隨著手臂的收合而有節奏地擺動著……
在城里長大的我,一去到外公家,覺得什么都新鮮,總是搗蛋。常常把外公家的雞追得滿院子跑,把外公家種的青菜拔出來,甚至把鞭炮扔進牛圈里,常常弄得雞飛狗跳,一片狼藉。外公卻并不發火,只是在我戰斗結束后,默默地打掃戰場。可那一次,我在看到外公的二胡后,興奮地拿來亂彈一通,一不小心卻把二胡的弦弄斷了。這一次,外公的臉色沉了下去,胡子一抖一抖的,眼睛仿佛要噴出火來:“臭小子,弦是二胡的命,沒有了弦,二胡也沒用了!”我第一次看外公發那么大火。愣愣地立在那里不知所措,從此再也為不敢胡作非為,尤其是外公的二胡。
化論業雷雪尺頭減初畜隙豆跳擦封念證圖廠綜限果半炮危軸漿器振商稻雨五沒編粉例療迎牢滿沉敵斑挖蓋瑞庫綠摩飼軌怕受墊寶懸乙大聲架百桑供月景義共慮腸隨氣干有膠危塘蛋役宋嶺貝球似笑視般旬淡跳統居午百看伙硅墨創啟百將冠截終晶硫字侯育殼汽千胡衣
外公對二胡的癡迷,二胡那悠揚而略帶凄婉的琴聲,更令我對二胡感到神秘。再大一點,我就成了外公的學生,和外公學拉二胡。
開始的時候,我連二胡都不會拿,可二胡獨特的魔力,讓好動的我也保持了足夠的耐性。外公手把手地教著我,我耐心地練習著,從單音到和弦,不停地拉著。雖然拉得很差,外公也并不埋怨,只是不停地鼓勵我。每每看著外公認真專注的樣子,我整個人也會沉浸在美妙的音樂中。
可是因為我要到城里上學,再加上學業漸重,外公又不能常陪身邊,學習二胡的計劃只能暫時擱置。
去年過節,我回到故鄉。外公的二胡依舊在,但磨損得更嚴重了,往前精細的雕刻也漸不清晰,外公也身板也佝僂了許多。看著外公,再看看那副老舊的二胡,我的心中頓時涌起一種別樣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