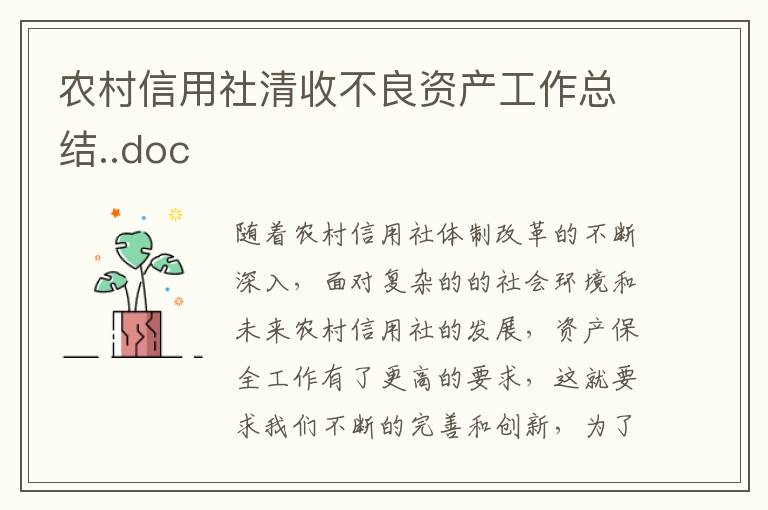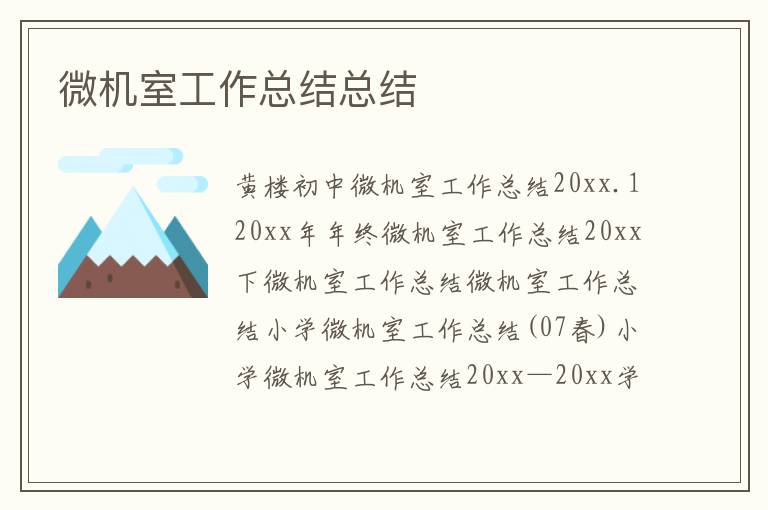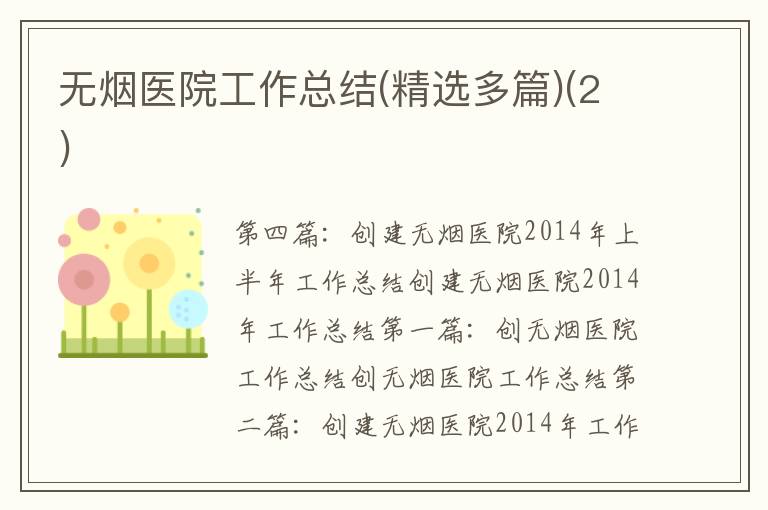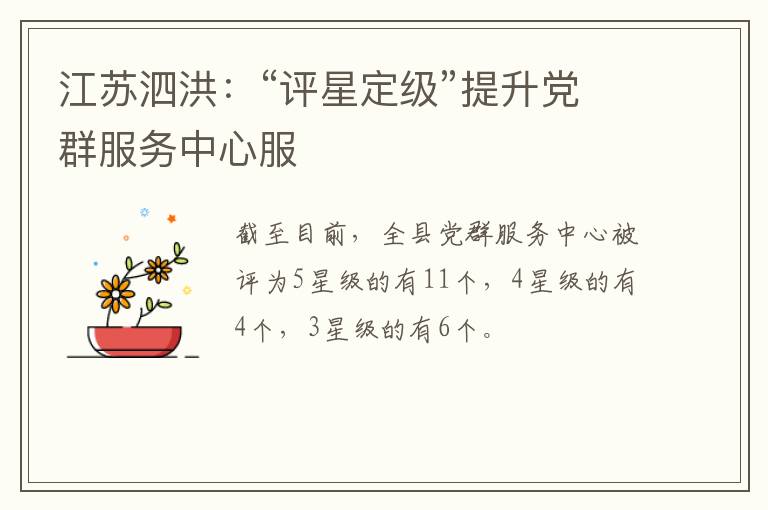2024年見識 學識 膽識優秀

在日常的學習、工作、生活中,肯定對各類范文都很熟悉吧。相信許多人會覺得范文很難寫?以下是我為大家搜集的優質范文,僅供參考,一起來看看吧
見識 學識 膽識篇一
“我帶你去的是白耀天白爺爺家里。他大學畢業后,當了23年的老師,桃李滿天下。“文化革命”以后,走上了廣西民族研究所的領導崗位。走入研究民族和歷史問題的行列。對了,白爺爺還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費孝通的高徒”,媽媽邊走邊說。我心想:費爺爺教出的學生一定很棒吧,不同凡響!
來到白爺爺家,那里擺設得古香古色,書架上擺滿了書,整整齊齊,讓我對他有了一定的敬佩之心。雖然白爺爺已經年過花甲,頭發也白了很多,但雙眼炯炯有神,身體還很筆直,走起路來腳步生輝,精神抖擻,銘滅不了我對他的敬佩之情。
與他交流時,他反應敏捷,妙語連珠,完全不像一個將近80歲的老人,那動作、眼神和姿勢不禁讓我嘖嘖贊嘆。
到面對面交流時,我了解到白爺爺的著作有:《西施考辯》《壯考》《壯族土官族譜集成》《依智高:歷史的幸運兒與棄兒》等。今年有一本叫《南天國與宋朝關系研究》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而由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壯族土官族譜集成》《依智高:歷史的幸運兒與棄兒》都受很多人喜歡。
還有一本《壯族社會生活史》字數最多,有180萬余字,已經完稿,正在校對。白爺爺還告訴我們:“有一次,一個人想用100萬買白爺爺的《壯族社會生活史》一書,他都不賣。”為了寫這本書,他不顧自己是花甲之年,親自到泰國去考查傣族文化、緬甸的克欽族文化,因為壯族的“媽媽”的發音是:“滅”,而他們的發音也相似等等。在那里,他每天都要翻山越嶺,行走在崎嶇的山路上,為了弄清某一個問題,他要從這個村寨走到另一個村寨。他這種不怕困難,不怕艱辛,務以求實的精神是值得我學習的。《壯族社會生活史》講的是我們壯族從出現到解放前發展變化過程。雖然,他講的這些我聽得不大懂,但是我以后要慢慢地弄懂我們民族的來歷和發展史。
去白爺爺家,讓我了解到我們壯族的許多知識,讓我見識到了編寫一本書,要花上幾年甚至一輩子的精力和心血,也學習到了很多課外知識,讓我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有了新的見識,這真是一堂受益匪淺的課啊!
見識 學識 膽識篇二
我們活在一個可大可小的世界,不過是走完一次難及百年的過場,甚至帶不走一路上任何的珍貴——請原諒我對生命如此的倚重。
世界是方的,也是圓的,是黑白的,也是迷彩的,眨眼之間,或許就成了另外一道風景;而造物偏偏給了我們可以用來感知的大部分——我們知道果凍的軟膩,知道辣椒的濃烈,知道山群的廣袤,知道歌聲的溫婉……由此我們又萌生了喜、怒、哀、樂,七情六欲,我們有了想望,有了對未來的期許,我們許諾了一個真誠的生命。
如此便是我歷來提倡人要見多識廣的根本所在,仿佛成了一種使命,一種“必須為”的默契。人貴在知,當然是一句箴言,踐行與否,便可稱為一種涵養。三歲小兒尚不具備基礎的認知,為時尚早;不惑之日又仿佛自認看透了世事,大抵是無法勸,也勸不動的;古稀之輩早早知曉了天命,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如此一來,青年人便無愧為最應當有此種涵養的群體,我曾在《對青年幾點真誠的期許》里寫道:年輕者,青年也;如初生之日,又如初起之風,未嘗經霜雨,最宜享難也。吾輩不失為世上生命力的群體,我們彼此的胸膛里積聚著一股股亟待爆發的力量,而見識常常是我們的指路人,它能給予我們施展拳腳的底氣,像一位現代化的哲人,指代著一個鮮活的世界。
我時常聽見同學們之于一場普通的電影、一句尚不明真假是非的論斷亦或是一則并不怎么撼動人心的新聞發出十分驚詫的贊嘆聲、驚詫聲,便發覺我輩如今對見識的“要求”愈發地低下去了,須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對我們來講不失為一種極大的嘲諷,倘使只將算計出一道艱深刻薄的習題或是做成一張滿分卷奉為主流,那我們倒不如都學做那瘋癲的范進先生去。對此李太白曾在《嘲魯儒》里嘲笑道:“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足著遠游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其實就是講一讀死書之人窮其一生將五經里的章句背得滾瓜爛熟,有人向他請教治國之策,他卻茫茫然不知所措,活像一個披滿一身學問大衣的啞巴,自是無用也。
我所謂的是得以同時調動我們的各個感官以及思想的見識,即真的見識,而若真的獲得,則必有一點大前提——“求知欲”。此求知欲非彼求知欲,此“求知欲”富于針對,并非泛泛而指。講的通俗一點便是依照你的心愿去求得這個知識,你要如其喜歡它,好比你十分厭煩那雨天,卻在無意間知曉了雨的形成,這在于許多尚不知曉的人興許是大見識,但你并不感冒,你得到了卻要將它爛在腸子里,不是萬不得已決不請它出來,這便又不能稱作見識。但若是個打小癡于氣象的朋友知曉了,他也許自此發生了變故,要摟著一本《雨兒是怎樣煉成的》徹夜攻讀完畢,便又稱得上見識了。這差異的制造者即是我所謂的“求知欲”。
我有幾個早早進了工廠打工的同學,他們時常抱怨生活簡直索然無味,整日整夜盯著一個機器來回地運作,實在苦惱。如此便是失去了最根本的“求知欲”,殊不知工廠里有多少饒有趣味的玩意兒!生活本身可以無聊至極,而我們要會找樂子,從一種景致、一種相貌、一種語言里汲取興趣的蹤影。若講得浪漫些,則仿若一位靜處于鬧巷間的老者正懷著深邃的目光待你去仔細攀談,那么你要用情地等待,用心的尋找,直到你“驀然回首”的一剎那,發現那位老者正在“燈火闌珊處”沖你招手微笑。
關乎見識這個問題,我這里僭引余秋雨先生一句不怎么相干的話:空虛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際。不錯,見識一廣便容易狂妄,這是人的通性——學問做的越深刻越是張揚跋扈。因而我們有一個極平常的現象,出過國的常看不起沒出過國的,城里人常看不起農村人。但我這里實在講不出孰是孰非,或講摒棄此種思想的法子我至今找不見,也許本不該反對人以群分的形態。李敖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大師,但他自許天下第一,此種狂傲尚且無從排遣,何嘗普通之人?見識不等同于學問,那么一個有見識的人也不等同于學問家,因而除卻見識本身之重要性,它的一些不可回避卻又難以處理的問題我們不必太過認真。
見識總是與日俱增、與時俱進,我們每日每夜清醒時的所作所為、所念所感統統都是見識,它不必要,卻又仿佛無所不在,甚至肆意游走于我們的意念之外,以至于我們往往后知后覺卻無法刻意而為。但若僅是這樣,又尚不足以,須知這見識自是隱隱行過了我們的頭腦,但其中的奧妙我們并不發覺,它更多的是受了冷遇,默默潛沉在深層的腦海間,然后隨著大潮來去,漸漸淡到了遠方,于是這寶貝丟了,再要找回來便成了大海撈針,為時晚矣。我們切莫學胡適之筆下的“差不多先生”,之于每天的見識,當盡量地抓住,盡量地回味,而后將它置于思想的境地,它便有了真意義,真可為你所驕傲。思之想之的時間是要擠的——信步之時、忙罷之時、將息之時……人人有生計,一位不滿月的孩子尚有牙牙學語的大事,又何況我們——我們大好的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