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全詩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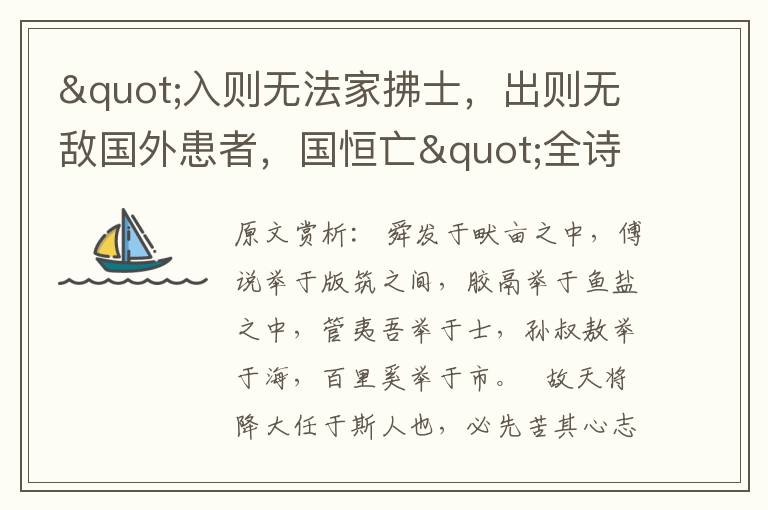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斯人 一作:是人)
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shùn fā yú quǎn mǔ zhī zhōng ,fù shuō jǔ yú bǎn zhù zhī jiān ,jiāo gé jǔ yú yú yán zhī zhōng ,guǎn yí wú jǔ yú shì ,sūn shū áo jǔ yú hǎi ,bǎi lǐ xī jǔ yú shì 。
gù tiān jiāng jiàng dà rèn yú sī rén yě ,bì xiān kǔ qí xīn zhì ,láo qí jīn gǔ ,è qí tǐ fū ,kōng fá qí shēn ,háng fú luàn qí suǒ wéi ,suǒ yǐ dòng xīn rěn xìng ,céng yì qí suǒ bú néng 。(sī rén yī zuò :shì rén )
rén héng guò rán hòu néng gǎi ,kùn yú xīn héng yú lǜ ér hòu zuò ,zhēng yú sè fā yú shēng ér hòu yù 。rù zé wú fǎ jiā fú shì ,chū zé wú dí guó wài huàn zhě ,guó héng wáng 。rán hòu zhī shēng yú yōu huàn ,ér sǐ yú ān lè yě 。
※提示:拼音為程序生成,因此多音字的拼音可能不準確。
譯文及注釋
譯文 舜在田間種地被任用;傅說從筑墻工作中被舉用;膠鬲從販賣魚鹽的工作中被舉薦;管夷吾從獄官手里獲釋,被錄用為相;孫叔敖隱居濱海被舉用;百里奚從市集中被舉用。 所以上天將要下達重大的使命在這樣的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內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饑餓(之苦),使他受到貧困(之苦),使他做事不順,用這些方法使他的內心驚動,使他的性格堅強起來,增加他(原本)不具備的才能。 人常常犯錯誤,這樣以后才會改正;心意困惑,思慮堵塞,然后才能奮發;(心緒)顯露在臉色上,表達在聲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個國家內)如果沒有執法的大臣和輔佐君主的賢士,國外沒有與之相抗衡的國家和外患的侵擾,這樣的國家常常會滅亡。這樣以后可以知道,憂慮患害使人發展,安逸享樂使人滅亡。
注釋(1)也:語氣助詞,用在前半句末,表示停頓,后半句將加以申說。(2)苦其心志:使其思想痛苦。心志,思想。志:意志,感情(3)勞其筋骨:使他的筋骨(身體)勞累。(4)餓其體膚:意思是使他經受饑餓之苦(以致肌膚消瘦)。(5)空乏:資財缺乏,即貧困。(6)他的所不具備的能力。曾,通“增”,增加。所不能,指原先所不具備的能力。曾益:增加。使性格堅韌(10)恒過:常常犯錯誤。恒,常。過,原意為過失,錯失,此處名詞活用作動詞,是犯過錯的意思。(11)然后:這樣以后。(12)困于心:內心困苦。困,被難住。于,在。(13)衡于慮:思慮阻塞。衡,通“橫”,梗塞,不順。慮:思緒。(14)而后作:然后才能奮起。作:奮起,指有所作為。(15)征于色:表現于臉色。意思是憔悴枯槁,顯露在臉色上。征,征驗(顯露,表現)。色,臉色、神色。(16)發于聲:表現在聲音上。意思是吟詠嘆息之氣發于聲音。發:表現。聲:聲音。(17)而后喻:(看到他的臉色,聽到他的聲音)然后人們才了解他。喻,明白,了解。(18)入則無法家拂(通“弼”)士:在國內如果沒有堅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佐君王的賢士。入:里面,此指在國內。則:如果。法家,守法度的大臣,。拂士:輔佐君王的賢士。拂(bì),通“弼”,輔佐。(19)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在國外如果沒有敵對的國家和外來的憂患。出:在外面,指在國外。敵國,勢力、地位相等的國家。(20)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這樣之后才知道因有憂患而得以生存,因沉迷安樂而衰亡。生于憂患:憂慮禍患使人(或國家)生存發展。死于安樂:安逸享樂使人(或國家)走向滅亡。(21)畎畝:田間,田地。(22)動心:使心驚動。
文言現象
通假字曾益其所不能:曾,通“增”,增加。衡于慮:思慮堵塞。衡,通“橫”,梗塞,不順。入則無法家拂士:拂(bì),通“弼”,輔佐。所以動心忍性。 忍,通“韌”,堅韌。這里作“使(他的性格)堅韌”。
詞類活用生于憂患(生)名詞作動詞,生存死于安樂(死)名詞作動詞,死亡
賞析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孟子所舉的例證是舜帝、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六人。
所謂“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為座右銘,激勵無數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奮起。其思想基礎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英雄觀念和濃厚的生命悲劇意識,一種崇高的獻身精神。是對生命痛苦的認同以及對艱苦奮斗而獲致勝利的精神的弘揚。
借用悲劇哲學家尼采的話來說,是要求我們“去同時面對人類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樂的科學》)
因為,痛苦與希望本來就同在。
說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太史公說得好: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們身處逆境的憂患之中,心氣郁結,奮發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緣故。
至于死于安樂者,歷代昏庸之君,荒淫逸樂而身死國亡,其例更是不勝枚舉。
所以,對人的一生來說,逆境和憂患不一定是壞事。生命說到底是一種體驗。因此,對逆境和憂患的體驗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說:“一切都經歷過了,一切都過來了!”這樣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什么磨難,沒有什么特別體驗的人生要豐富得多,因而也有價值得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