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物解藝 要在究竟——周永健的治學(xué)、藝術(shù)與修養(y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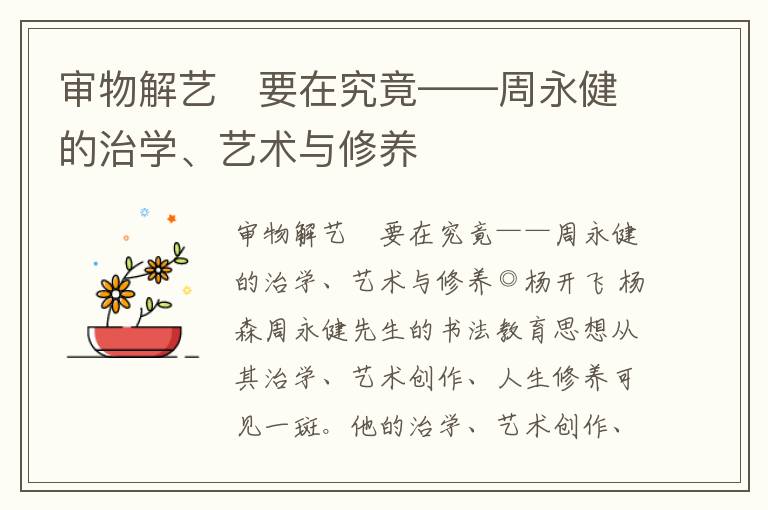
審物解藝 要在究竟——周永健的治學(xué)、藝術(shù)與修養(yǎng)
◎楊開(kāi)飛 楊森
周永健先生的書法教育思想從其治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人生修養(yǎng)可見(jiàn)一斑。他的治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人生修養(yǎng)三位一體,對(duì)當(dāng)下高等書法教育有矯正之功。
一位以藝術(shù)托生死的人,總是通過(guò)藝術(shù)創(chuàng)造實(shí)現(xiàn)其人生目標(biāo),藝術(shù)標(biāo)明了人的高度和深度。人是藝術(shù)的主宰,只有杰出的人,才可能創(chuàng)造杰出的藝術(shù),所謂人成則藝成。藝術(shù)的終極關(guān)懷指向人,既修己又修人。人既是藝術(shù)作用的最終目標(biāo),又是藝術(shù)活動(dòng)本身的締造者。人在參與藝術(shù)活動(dòng)時(shí)如何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呢?當(dāng)我們思考這樣一個(gè)重要的問(wèn)題時(shí),應(yīng)該從一直探尋其究竟的周永健先生那里得到有益的啟示。因?yàn)檫@是每個(gè)藝者必須深入思考的課題。
“究竟”作為一個(gè)佛教名詞,它一般指佛典里最高深的事理。《大智度論》七十二云:“究竟者,所謂諸法實(shí)相。”《三藏法教》九云:“究竟即決定終極之義。”周永健先生依佛說(shuō)事,努力求證治學(xué)、藝術(shù)與人生修養(yǎng)的至境至理。
一、治學(xué)之究竟
周永健先生在2008年《書畫世界》第一期和《書法》第四期兩次發(fā)表明軒題跋。
唐人書秀逸中透生死剛正之氣,此舊日讀帖余所未得也。或謂人之閱歷為助,非至?xí)r日而不易悟也。以是余舊日所輕之書,判之固有乖誤,審古今不類,前賢得名皆非無(wú)據(jù),此峰高途殊,俗庸所難至也。故求知為學(xué),弊在我執(zhí),審物解藝,要在究竟。物本不物,好惡皆在人情,道無(wú)增減,損益本乎人心。(參見(jiàn)2008年《書畫世界》第一期第51頁(yè)和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5頁(yè))
以唐人書法為例,周永健先生深刻揭示人對(duì)客觀事物的認(rèn)識(shí)常常因受到各種主觀因素制約而發(fā)生誤解和錯(cuò)覺(jué)。這種誤解并不僅僅在觀念,最可怕的是它常常支配著我們的行為,導(dǎo)致我們最終失去認(rèn)識(shí)真理的機(jī)會(huì),而永遠(yuǎn)成為一只迷途的羔羊。洞察事物本質(zhì)絕不可能一蹴而就,認(rèn)識(shí)必須逐步深入,這就要求人們?cè)谥螌W(xué)上必須具備探求究竟的方法和態(tài)度。
藝術(shù)學(xué)習(xí)貴在究竟,只有具備了認(rèn)識(shí)的高度和深度,繼承和創(chuàng)新才有意義,在探求究竟的過(guò)程中才能夠真正提升自己價(jià)值,故治學(xué)必須探求究竟。首先是肯花時(shí)間,肯下苦功。真理的認(rèn)識(shí)需要一個(gè)曲折而又漫長(zhǎng)的過(guò)程。其次要不斷積累知識(shí),錘煉技能,增加閱歷。認(rèn)識(shí)“唐人書秀逸中透生死剛正之氣”需要書法學(xué)習(xí)長(zhǎng)期累積的知識(shí)和技能,更需要傳統(tǒng)文化作支撐。沒(méi)有專業(yè)知識(shí)和技能,沒(méi)有相應(yīng)的文化背景,要想認(rèn)識(shí)唐人書法所蘊(yùn)含的儒家生死剛正的品格,無(wú)異于緣木求魚。再次要努力提高書法鑒賞能力。只有具備這樣一些條件,我們才可能逐步領(lǐng)會(huì)藝術(shù)的真諦,最終破解奧賾,實(shí)現(xiàn)人的價(jià)值的全面提升。
探尋究竟,是治學(xué)所必具的品質(zhì),同時(shí)也表明為藝者治學(xué)的方法和態(tài)度。治學(xué)中保持追究精神是為藝者成就藝術(shù)勝境的前提和基礎(chǔ)。
二、藝術(shù)之究竟
任何一個(gè)從藝者都必須明白造就藝術(shù)所經(jīng)歷的階段,以及自己當(dāng)下所處的位置和努力方向,對(duì)藝術(shù)層境的探究會(huì)使為藝者不斷推進(jìn)藝術(shù),最終抵達(dá)藝術(shù)的至高境地。周永健先生認(rèn)為書法藝術(shù)有三個(gè)層境。
書道三層境:修相、修藝、修道也。修相者緣相得相,以形式表現(xiàn)為皈依;修藝者緣相寄藝,以個(gè)性顯豁為佳境;修道者緣相破相,發(fā)意凈意,以心性修為為根基,以真覺(jué)、正慧為根本。此境分三者,因果互在,要之為一:非相無(wú)以載情意,非情意無(wú)以參真?zhèn)危环窍酂o(wú)由悟生滅,非生滅無(wú)由證空相。蓋道律之在,萬(wàn)物堪辨,理一分殊,豈獨(dú)書然?!是故小聰偏執(zhí),大慧不出,假我不破,真我難立,真我既立,則物我無(wú)隔。人藝一體,換骨上賓,書進(jìn)乎道也。此緣相修藝,借藝成人之法,假書道之用大矣!(參見(jiàn)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7頁(yè))
周先生在藝術(shù)上是一個(gè)嚴(yán)于律己的人。他在給李剛田的信中說(shuō):“我常在內(nèi)心苛求自己,所以對(duì)自己的藝術(shù),很少有滿意的時(shí)候。”(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5頁(yè))這種苛求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方面是藝術(shù)理論的探求,思考個(gè)人藝術(shù)行為的最大價(jià)值所在;另一方面是創(chuàng)作實(shí)踐對(duì)理論的驗(yàn)證。藝術(shù)的探索過(guò)程是艱苦而又漫長(zhǎng)的,而看到由求索所取得的成果時(shí)是無(wú)比歡欣的。先生把自己的生命智慧奉獻(xiàn)給藝術(shù),始終表現(xiàn)出一種勇猛無(wú)畏、積極進(jìn)取的精神狀態(tài)。他所提出的藝術(shù)三境可以看作他為自己設(shè)立的標(biāo)桿。他對(duì)自己的不滿確證了他在藝術(shù)上的不甘平庸,追求卓越。他敢于正視自己的缺點(diǎn),所以他對(duì)自己時(shí)常不滿。他時(shí)常挑燈夜戰(zhàn)——“我與我周旋久,我自知我”(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62頁(yè))。他時(shí)刻努力超越自己,希望跨入藝術(shù)的至境。他希望自己是一個(gè)修道者,“緣相破相,發(fā)意凈意,以心性修為為根基,以真覺(jué)、正慧為根本”,實(shí)現(xiàn)借藝成人之目的,發(fā)掘書法藝術(shù)之究竟。
在書法三層境中,修相是基礎(chǔ),修藝是階梯,修道是究竟。在眾多為學(xué)求藝者當(dāng)中,修相者眾,修藝者少,修道者少之又少。修相者只有破除“我執(zhí)”和“所知障”(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yè)),才能一步步晉級(jí)為修藝者,最后成為一個(gè)修道者,獲得真覺(jué)大慧。周先生的“三層境說(shuō)”,不僅表明了他的心路歷程,而且也彰顯了他追求藝術(shù)究竟的決心、信心和能力。他始終對(duì)自己的藝術(shù)、心性表里觀照,在探尋藝術(shù)至境的過(guò)程中,不斷地對(duì)自己進(jìn)行分析解剖,查明制約自己藝術(shù)進(jìn)步的心理羈絆。
余識(shí)書道、人生三層境,傾心仰慕而不達(dá)者蓋塵染未凈,利祿未去故也。(參見(jiàn)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7頁(yè))
先生信守“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古訓(xùn)。因人治藝,以藝醫(yī)人,人藝一體,以心為本。他主張“為藝者治藝亦當(dāng)治心,似此,方能心無(wú)掛礙,心藝無(wú)間而與造化游”(參見(jiàn)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8頁(yè))。我們深切地感覺(jué)到先生在追尋藝術(shù)究竟的時(shí)候,始終把矛頭對(duì)準(zhǔn)自己,叩問(wèn)藝術(shù)究竟,以及不達(dá)究竟之究竟。先生嚴(yán)謹(jǐn)治學(xué),苦心孤詣,勤奮進(jìn)取,磨礪自我,令人肅然起敬,堪稱當(dāng)今為學(xué)治藝之楷模。
三、人生修養(yǎng)之究竟
書法和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聯(lián)系異常密切。只有站在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上,才能對(duì)書法所牽扯的一系列問(wèn)題給予清楚而正確的解答。借藝修人,所修之人必須符合傳統(tǒng)文化的價(jià)值判斷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只有具備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的人才會(huì)深刻領(lǐng)悟書法藝術(shù)最高境界。周先生深諳此理,在向著書法最高境界修煉的人生旅途中,始終注重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尤其是佛學(xué)修養(yǎng)。這既展示了他對(duì)書法藝術(shù)杰出的理論駕馭能力,更表明他內(nèi)心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固有的虔誠(chéng)與尊敬。
舍佛學(xué)而為藝、論藝,雖可以世間聰辨成一規(guī)模,但到底無(wú)法表里觀照,還是小家偏局(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49頁(yè))。
真、善、美、慧乃佛家之語(yǔ),較世間論藝之功用,更為完備、嚴(yán)密(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6頁(yè))。
周先生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摯愛(ài)有加,他反復(fù)閱讀《道德經(jīng)》《莊子》《論語(yǔ)》《金剛經(jīng)》《華嚴(yán)經(jīng)獅子章》等,于是儒、道、釋的宗師,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也就成了他最景仰的人。三十四歲之前,他主要研讀儒道兩家。三十九歲以后開(kāi)始系統(tǒng)學(xué)習(xí)佛學(xué)的主要架構(gòu)和典籍,他的人生觀、藝術(shù)觀由此發(fā)生了重要轉(zhuǎn)變。正是這種長(zhǎng)期的積累和學(xué)習(xí),先生對(duì)傳統(tǒng)文化感悟頗深。
深入傳統(tǒng),沒(méi)有心態(tài)不行,憑小聰明去感受,終不得其三味。現(xiàn)代人的心態(tài)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與古人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jì),故現(xiàn)代人學(xué)傳統(tǒng),極少深入者。我學(xué)傳統(tǒng)常取心境轉(zhuǎn)換法,進(jìn)入傳統(tǒng)時(shí),放下一切,浸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歷史氛圍和藝術(shù)氛圍中,頗像影人進(jìn)入角色,似此,自覺(jué)與古人有會(huì)心時(shí),觀其藝,也能產(chǎn)生較多的共鳴(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6頁(yè))。
對(duì)于一個(gè)書法藝術(shù)家來(lái)說(shuō),傳統(tǒng)文化是他必備的人生修養(yǎng),就這一點(diǎn)沒(méi)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可惜的是,當(dāng)今多數(shù)藝者,或以技說(shuō)技,或就藝論藝,根本不重視也不能夠從更高的層面認(rèn)識(shí)傳統(tǒng)文化對(duì)書法藝術(shù)的重要性。先生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針砭包含著他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從藝者的某種焦慮。傳統(tǒng)文化本身遭遇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漠視,使得藝者進(jìn)入傳統(tǒng)缺少良好的文化語(yǔ)境。大多數(shù)為藝者的腳步,因此被攔截在傳統(tǒng)文化的大門之外。只有個(gè)別人除外。先生在深入傳統(tǒng)文化的學(xué)習(xí)中找到知己,知難而進(jìn)。先生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精研是人生修養(yǎng)的究竟之學(xué),也是成人取慧的關(guān)鍵之學(xué)。
先生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作用于他的人生,則人生充滿智慧;作用于他的藝術(shù),則藝術(shù)彰顯風(fēng)采。在儒家方面:(1)先生崇尚清剛之氣。他經(jīng)常畫蘭以養(yǎng)清氣,以出世志做入世事,表現(xiàn)他對(duì)清潔人格的向往;他常懷濟(jì)世之志,期其有為,不謀私利,無(wú)欲則剛,表現(xiàn)了一個(gè)儒者的風(fēng)范,其清剛之氣行于世,施于人,不可磨滅。其書藝與人無(wú)二,覽其書,清剛之氣,直面撲來(lái)。(2)先生重視法度,適時(shí)使用。于書協(xié),于出版,于研究生教育,于藝術(shù)理論、創(chuàng)作、研究,先生均有作為,分身有術(shù),運(yùn)籌得法,忙而不亂,進(jìn)退自如,彰顯人生智慧;書法方面,他推崇魏晉筆法,分類辨析,法眼獨(dú)具,他認(rèn)為晉人書法復(fù)雜的技法(絞、翻、轉(zhuǎn)、折、曲、駐)帶來(lái)豐富的筆意,造成細(xì)節(jié)的無(wú)限可讀(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103頁(yè))。先生在當(dāng)今草書創(chuàng)作中頗得晉人絞轉(zhuǎn)之法,盤旋轉(zhuǎn)折,游刃有余。在道家方面,周先生崇尚自然。生活上,他作風(fēng)簡(jiǎn)樸,不事張揚(yáng),散淡閑適之旨,溢于言表,與人交往,真誠(chéng)直率;藝術(shù)上,他認(rèn)為“自然是一切藝術(shù)的法則”(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219頁(yè))。“若著意于意,則意見(jiàn)矜持,多為生造而不自心中流出。如泥拘于法則法乏生機(jī),雕琢有跡,難與造物者游”(周永健:《風(fēng)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177頁(yè))。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一切服從自然,全身放松,不知使力,不知使氣,不知成法,不知經(jīng)營(yíng),情以跡現(xiàn),一任流走。他將道家的自然觀化用到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當(dāng)中,賦予了新的時(shí)代內(nèi)涵。在佛家方面,他更是全面地吸收,化用無(wú)方。他稱佛學(xué)是智慧之學(xué)。生活上,他以慈悲為懷,樂(lè)施善救,滿懷愛(ài)心,書界有口皆碑;剖析事理上,采取了佛學(xué)唯識(shí)中觀的思辨方法,以空為本體,識(shí)空證慧;藝術(shù)上,為藝者應(yīng)求一“慧”,應(yīng)付出一生之力,磨煉心性,澄懷靜慮,他的碑派書法作品雍容典雅,靜穆幽深,境界博大。近期發(fā)表在《書法》雜志的榜書“百年孤獨(dú)”(參見(jiàn)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6頁(yè)),充滿佛教情懷,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佛學(xué)修為。
周永健先生的治學(xué)、藝術(shù)與人生修養(yǎng),在探尋究竟的各個(gè)方面取得很多經(jīng)驗(yàn)和成果。他提出“審物解藝,要在究竟”堪稱為藝者的不刊之論,對(duì)凈化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藝術(shù)風(fēng)氣,深化藝術(shù)創(chuàng)作質(zhì)量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他讓我們深深感到究竟是一種為學(xué)求藝的方法,同時(shí)也是一種治學(xué)態(tài)度,更是一種鍥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它始終引導(dǎo)著藝者向著高處、更高處攀登,永不止步。沿著究竟之途必將抵達(dá)創(chuàng)造之巔,標(biāo)示出人在歷史進(jìn)程中所應(yīng)具有的深度和高度。
當(dāng)代高等書法教育應(yīng)該回歸傳統(tǒng),積極吸收前代書法家們?cè)谥螌W(xué)、藝術(shù)、人生修養(yǎng)方面的體悟和成果,取長(zhǎng)補(bǔ)短。取他人之規(guī)矩,開(kāi)今人之面目。讓高等書法教育既有文化傳統(tǒng)的血脈,又有當(dāng)代人的智慧和經(jīng)驗(yàn)。
楊開(kāi)飛,博士,寧夏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書法理論與創(chuàng)作研究工作。現(xiàn)為中國(guó)書法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寧夏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寧夏書法家協(xié)會(huì)主席團(tuán)委員,兼任寧夏青年書法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寧夏文史館研究員,甘肅張芝書法院特聘教授,江蘇劉海粟美術(shù)館特聘教授。楊森,寧夏大學(xué)土木水利工程學(xué)院國(guó)防生,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有濃厚的興趣,愛(ài)好書法寫作。









